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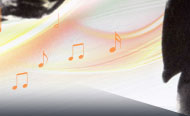

要说的,并不真的是“中国电子音乐”,而是“大陆非学院派电子音乐”。学院派当然有电子乐,而且还有国家级的电子音乐中心,有钱有设备,有教学创作研究和竞赛交流。前些年他们刚刚发现电脑,疯狂地用MIDI(注1)手段模仿真实乐器,创作了大量垃圾。我偶然得到过一张唱片,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主任、“中国现代电子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张小夫当年给九运会作的长篇巨制——该泰斗居然拿电子音色模拟管弦乐队,其庞大夸张、其轻浮廉价、其难听无聊,简直无以复加。而今他们也与时俱进,终于回到了欧洲
学院派的正路上来。偶然音乐、具象音乐等等传统理论,逐渐有了新的、本土化的实践,而国际通行的电脑音乐和学院派先锋电子乐,也可以在年轻的中国音乐家身上找到回应。
在谈到电子乐的时候,我不会提起上海学院派擅长的新世纪音乐,尽管它融合了民族、古典和可以洗涤心灵并和宇宙沟通的缥缈的电子声音。众所周知,把它们的电子乐部分改成弦乐可能还更舒服一点。
也不想说1981年,法国流行电子乐大腕让·米歇尔·雅尔来过中国之后,国内风行一时的合成器流行乐。像80年代朝阳国际电子乐队的翻版,或者何文彪改编流行歌曲的畅销盒带。这些声音曾经让很多人激动莫名,以为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故事必将实现,而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当时的做法非常简单,调出电子合成器预设的音色,选择节奏型,演奏旋律和其他部分。一种朝气蓬勃的特征,体现在由高速而连贯的单音构成的旋律中,还辅助着明亮、单调而同样高速的节拍,它延续了西方电子流行乐乐观的科幻、未来主义情绪,也折射着整个社会激动而天真的追求。不过归根结底,这还是电子设备为流行乐服务,而不是用自己的器材建立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美学、自己的脉络。这就像二战以后西方学院派用包括电子设备在内的各种手段为先锋音乐理论服务,就像合成器和电脑刚开始大规模生产销售的两个时代,都曾经为模仿、取代流行歌曲或古典音乐原有配器而服务。况且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还是商业音乐最基础的部分。
如果说乐器被演奏,用音乐语言创造意义。那么也可以说在乐器的时代,人们围绕着意义创造了一套价值和美学规则。但电子乐不是意义的奴隶,在意义被最大程度复制的年代,它宁肯是废话——相对于音乐语言的组织、条理、规则,电子乐,无论是电子舞曲,还是实验电子乐,都从不表达意义的地方找到了新的语法。
节奏、旋律、和声,西方正统音乐的三个要素。加上音色和歌词,流行(广义的)音乐所重视的另两个要素,所有的意义都从这里出发。而电子乐要么成为它自己,要么做别人的替身,就看它是否重写规则。
先说迪斯科,它起源于黑人的疯克(funk)音乐,为顺应消费性的青年文化,为疯狂的跳舞活动而加重了4/4拍的低音部分,并越来越舍不得写旋律,拼命反复简单的乐句。70年代中期,迪斯科如日中天。它是歌曲的变体,忠实于传统的曲式和演唱,主歌副歌华彩,一个也不能少。直到1985年前后,芝加哥、纽约等地出现浩室(house)舞曲,曲式被抛弃。鼓机制造不断重复的4/4拍节奏,混音台可以把节奏和歌声混到一起去,再加上自己做的音效,地下跳舞运动就此诞生——一个以化学软毒品、中性文化和回归自然为主题的集体青年亚文化开始了。
参加过300多张专辑创作的比尔·拉斯维尔(刘索拉《蓝调在东方》的制作人)说过:“我不是重新混音,因为原来的作品就是声音组合的一种方式,而我在用另一种方式组合”。剪下他人或自己的作品片段,或仅仅一个音,重新拼合起来;对这样的素材进行调变和转换,加工成全新的声音素材,然后进行组合;让素材在软件的自由选择下偶然随机组合,并利用如此产生的失真的非乐音,或者主动地利用软件进行选择和拼贴控制;使用未经处理的数字信号,得到物理学意义上的纯粹的声音(注2)……简单地说,也就是把语言拆解为废话,然后加以利用。
这些手段其实也在被各种流行非流行音乐家使用,像流行大牌广播迷乐队2003年的专辑,就用到了欧洲地下电子场景里的噼啪脉冲。但手段背后的哲学,一旦上升到音乐作品的整个系统,那么这就是去中心化、对局部表现力的瓦解、通过结构观察声音,以及,把东方化的直觉和法国人的后现代哲学和新的科技手段、科技哲学组合起来的音乐乌托邦。用DJ Spooky(注3)的话说,就是“从我们自身被异化的意识中提取元素,将它们重新组合,从旧的语言创造新的语言,通过着种方式反映被我们称为家园的混乱喧嚣的现实,也许是一种寻求对高速发展的科技作用于我们集体意识上的损伤的和解方式。”
1997年,北京的“叛逆知识分子”郝舫写下了《电动灵魂》,这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和梳理电子舞曲的文章,第二年,他的另一长文《噪海》又成为国内最早的噪音(或者不如说非乐音)音乐文化论文。郝舫当年说到的音乐,如今才被少数人引为酷之标签。而1996年在深圳做了“数字之梦”电台节目的倪兵,如今是DJ和跳舞活动策划人。北京的名DJ、电台主持人和一家跳舞俱乐部的股东张有待,在那个时候主要通过开唱片店卖走私CD、在酒吧放唱片来传播电子乐。
和他们不用的是,我现在不是在追忆中国的音乐家如何焊接电路、发明规则,而是他们如何在残缺、模糊的西方音乐影响下创作。请注意,他们对电子乐一知半解,而不是像任何一个美国小孩那样,从胎教时就知道什么是DJ,谁在抄袭谁,而谁又是学院派和街头混混的混血……他们通过盗版、走私和下载mp3来搜寻支离破碎的音乐地图。影响的焦虑?不!中国是一个土鳖的国度,做土鳖的好处是,你不会那么焦虑,你只需要行动,你稀里糊涂地,就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也是1997年,DJ组织“奶酪”举办了第一次长城锐舞派对(注4),著名的“保持联络”酒吧也做了第一场地下锐舞活动,以前的吉他手、后来的名DJ翁翁在三里屯一带玩最前卫的舞曲,中国人刚开始明白DJ并不是喊“一二三四跟我来”和放口水歌的职业……DJ重新组合别人的语言,让新的废话过夜即逝,只留下重复节拍里漫游太虚的汗。和中国青年曾经想象过的摇滚英雄不同的是,DJ废除了表演者的中心地位(一个中心和若干分支构成的扇形或圆形的剧场模式),他更强调与舞者的平等互动,而意义,要在一个网状的互动结构里激发出来,我们管它叫,气氛(英国圈里人说的vibes)。
仅仅是在1999年到2000年,以北京为中心的地下跳舞运动不正常地发达过一阵子,如今除了上海,各地的电子舞曲都仍然被守旧的迪斯科压制,尤其是北京,除了两家俱乐部和几个偶尔搞点活动的酒吧,电子舞曲已经被白领文化彻底腐蚀干净了。那年头,一票死磕新鲜事物的战士,和若干野心勃勃的DJ,在各个俱乐部和户外场地甚至普通的酒吧创造过短暂的颠峰。DJ不用照顾顾客的要求,顾客则恨不得一晚上跑3个场子。但不过一年,他们就玩累了,在白领和外国商人的冲击下撤退了。
而上海有Pegasus、Buddha、May、Park
97、Guandii、Mazzo、Taiphong、Rojam这些国际级的跳舞俱乐部……上海有国际性和全国性的DJ大赛……上海有追逐时尚的传统。因此上海是今天中国惟一在跳舞的城市,这里的年轻人也以善于辨识电子音乐而著称。消费在变化,上海人不但在艺术中心和游轮上跳舞,甚至会在郊外的仓库进行秘密聚会(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药物)。音乐口味迅速带动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分形,上海说唱乐高手MC
唐,就曾经在他的作品《2001拗造型》里描述了各种街头服饰的流派。
1995年,窦唯发表第二张个人专辑《艳阳天》,这是一张采用了大量电子手段的低调歌曲专辑。1998年,中国最早的电子乐队超级市场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模样》,但实际上这是一张采用传统歌曲结构的另类电子流行乐。同年,另类乐队“苍蝇”的主唱丰江舟在台湾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电子乐专辑,《恋爱中的苍蝇》,它应该是看做中国最早的电子乐作品——而且是风格激进的地下电子音乐。1999年,窦唯发表了和名制作人张亚东合作的《山河水》,一张电子乐和英式摇滚、后摇滚交织起来的专辑。超级市场发表了音乐性更强,也更复杂的《七种武器》。崔健为《鬼子来了》做的插曲,是一首被描述为“鼓打贝司”的时髦电子乐。张亚东经过对英国另类、时尚音乐的长期学习,也在香港发表了一张相当商业的电子流行乐专辑《亚东》。
现在已经和即将正式发行专辑的电子艺人还有A4、毛豆、虎子、Sulumi、Password和DJ
Micky、Ronez、泰然、卢小旭和靳松。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则是广州的主流舞曲乐队与非门和武汉的跳房子。
此外,1999年,西安的大学生Flox在网上地下发行了专辑《样品:
98-99》那是一张富于想象力的舞曲专辑。之后的几年里,那些沉浸在亚文化生活中的中国人,逐渐从网络、小型唱片店以及演出现场买到了更多的电子乐。因为缺乏商业的回报,中国电子音乐向着越来越前卫、越来越纯粹的方向前进,演出和唱片,甚至相关的网站和杂志,都具备了最鲜明的亚文化特点——在自己的世界传播、用自己的暗号交流、以自己的标准来划分价值。
我们必须记住的名字,包括创作不同类型音乐的王凡、从民谣摇滚转向电子乐的王磊、上海的大学生乐队艾塔(Aitar)、Dust
Box和ISMU、北京的唱片零售商me:mo、桂林的会计周沛(Ronez),以及正在获得声誉的fm3。其中20岁出头的一批新人,尤其锋芒毕露——因为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摇滚乐影响,直接从声音艺术、实验电子乐中获得营养的音乐家,P2P软件和MSN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利器。这两代人,受不同的影响,靠不同的本能和观念,做不同的音乐,在不同的方向上为中国电子乐(主要是实验电子乐)树立了高度。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发现了信息时代的小众是多么有力——那些全世界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几百人知道的音乐家,在中国有着殊途同归的知音和另起炉灶的竞争者,而更多的中国人却对这些同胞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在脱离了传承系统的前提下,这些土产音乐家(例外的是,fm3乐队有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美国人)创作出了中国的声音。狂暴的噪音,或者静到虚无的声音,川剧和琵琶的片段,或者毫无文化背景的杂音,都在传递着中国的情绪和中国的思维。这也是他们比技艺高超的DJ更受人尊敬的原因。
在2003年11月的最初4天,实验电子乐领域的雷达对准了中国。一个叫“声纳2003·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的活动在北京举行,近来密切关注中国新音乐动态的权威杂志《连线》(Wire),刚刚发表了对fm3和一些年轻音乐家的评论,马上又为他们的现场表演开辟了版面。当然,这个活动倍受关注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中国的新声,而是卡科夫斯基、赫尔穆·谢弗等国际大腕的到来。策划人姚大钧,旅美台湾音乐家和乐评人,几年来通过一个网络电台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年轻音乐家,他相信让这些甚至有的还没有现场表演经验的小伙子和国际明星同台表演是值得的。“声纳”原本是西班牙一个电子艺术节的名字,近年来几乎所有最火的实验电子音乐家都在那里表演,多媒体艺术方面也是名声赫赫,借用这个名字,显然是一种暗藏的雄心。
在描述起来热火朝天的中国电子乐场景中,无论是市场的冷落,还是资讯的残缺,都没有阻拦住舞曲编辑机、音源、滤波器、模拟唱机、苹果电脑、软件和插件、混音台、数字录音机、声卡、MIDI键盘……这浩荡大军的步伐,其实不是在改变中国的音乐市场,它改变的是编织在年轻人和更年轻的人思维、感觉和表达中间的语言之网。这些老音乐家闻所未闻的机器,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从声学物理实验室流传出来的,可是,它们普及了——不需要系统和专业的学习,人人可以玩音乐,而且,甚至可以在卧室完成音乐,连录音棚都不需要。
而这些年轻人目前最大的麻烦,不是没钱,而是语法的混乱。
几年前丰江舟依靠理性和智慧完成的认知,西方人用从小浸泡在其中的方式完成。更多的中国音乐家则耽搁在表面,技术、器材、手法、疯狂搜集新唱片……但是一座唱片之山也是一座声音的垃圾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去寻找宝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去寻找宝藏和垃圾的谱系。我们学习得越快,就越容易在一张专辑里装下所有的风格。毛豆的《粉》是这样,虎子的《叛客》是这样,A4的《动员日》也是这样——而这些都是我们能脱口而出的不错的音乐,和充满希望的音乐家。
每一个声音都不是偶然的。它像一万颗冰雹中的一颗一样,凝聚了整个天空的信息——罗兰公司生产的TB-303、TG-808这些设备,和世界上最早的民用合成器“穆格”一样,确立了经典的音色,今天还在使用它们的人,是为了制造怀旧的气息。后数字时代的声音,纯净而平凡,毫无乐音那种丰富的表现力,这是因为音乐不再统治耳朵,科技服从心灵的回归而不是为了装饰,这是一套新的科技哲学。在新的作品中,如果出现大段他人作品的采样而不加修改,那一定是故意突出原作的信息,让听者发笑或者感伤,因为采样的道理,是和环保再生材料一样,要求再加工、更高的品质和更多的个人色彩——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来龙去脉,都和创造者脑子里的音乐坐标系有关。
100多年来,铁路和城市变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当那些自然界不存在的声音变得林立,自然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当电子的咚呲或者噼啪从数字信号转换为你耳机里的声波,技术也就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或者不如说,我们的身体和环境都在进化,当fm3难以察觉的低频弥漫了整个空间的时候,你会相信这毫无表情的50或200赫兹脉冲,就是此时此地最自然最感人的禅意。
(注1)MIDI:1,Music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乐器数字接口)的缩写,1980年,为电子乐器、电脑和其他数字或非数字相关设备的数据传输而确定的国际标准。2,应用MIDI接口的一整套音乐制作设备的代称。3,中国特有的“MIDI音乐”的简称,指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简陋的、当时看起来时髦的、使用电脑等MIDI设备制作的学院派或流行音乐,主要特色是使用数字技术,模仿和改动真乐器的音色。4,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简称。
(注2)此处提及的技术和理论,有时候被描述为cut and
paste(剪贴)、mod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调变与转换)、statistic random(随机选择)、click and
cut(点击与剪切)等等。顾名思义,作曲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
(注3)DJ
Spooky:全名DJ Spooky That Subliminal
Kid(DJ幽灵,那个潜意识小子),美国黑人DJ、电子音乐家、乐评人、科幻小说家、哲学学者。他的乐评对同行影响很大,但一些作品是杰作,另一些则毫无建树。
(注4)锐舞派对:rave
party。90年代兴起的户外大型跳舞活动,特征是新的电子舞曲、自发性、使用药物和参与者回归自然的倾向。一年一度的长城锐舞派对,是国内少见的此类活动。颜峻